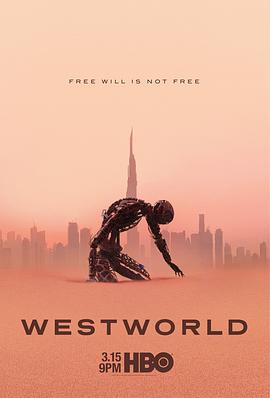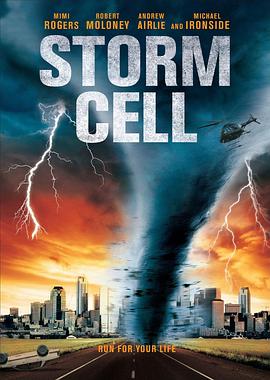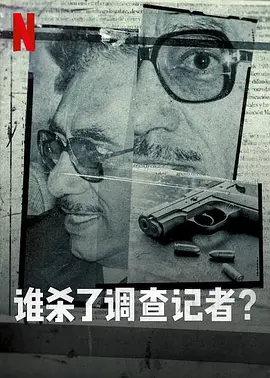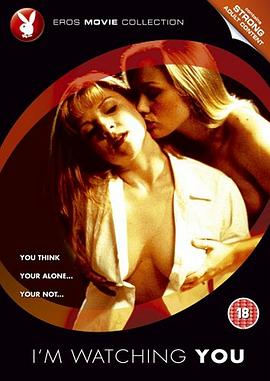从远方里寄居在伊斯坦布尔的小镇青年,到枯草中流放在安纳托利亚小镇里的知识分子,我相信锡兰已经在自己影像序列里,构造了一个和契诃夫的戏剧一样伟大的世界,里面充满了一个个悲切的无能的挣扎的个体,而这确是属于锡兰自己的白银时代。锡兰的水准之作,此次的男主角虽然也属于知识分子,但状态更贴近普通人,这是一个满是缺点的男性,一个热爱爹味教育、好妒自私、自以为是的小镇老师。他在掉落式的百无聊赖的工作里,可以说是再一次地凋落,最终以近乎渴求的方式在一个小女孩面前寻求尊严。这依旧是一个契诃夫式的文学电影。片中的两个女性好有力量,一个虽然是残障人士,但完全掌控着自己的欲望关系和情感关系,一个是处在下位者的女学生,面对反反复复的锡兰近几部电影的主角都是失败的知识分子,他们刚开始抱有某个明确的目标,随着剧情发展,目标无法实现,对自身命运逐渐失去控制。作为男性的锡兰,以充满审视的笔和摄影机为手术刀,将男主角剖开,其虚伪、自私的本性被一览无余。锡兰的对话是文学的,后几场会话精彩绝伦。他的视觉则是油画的,设计了独特的透视光,很多场景精美得像点缀着宝石的织物,像博物馆里的古典绘画返回到现实。本片雪的场景让我想起勃鲁盖尔。几用三个小时酝酿许多人一生的厌男情绪,看到后面的我面部都扭曲了。男性习惯了作为上位者操纵权力关系,一旦他受到较之更高的权力的鞭笞,就开始变本加厉地向下施力。如果这种向下的力也被打破,他便无所适从。但是男人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他如此善于编织一套对自己有利的叙事,甚至不惜牺牲同僚或是共谋者,也要拾回上位者的姿态。对于他们惊人的自洽能力,我们别无他法,只有不陷入他所设下的语言的圈套,随他做自己故事的主角,由他被狠狠说教到,锡兰已成为绝对理性的社会学导演,人物的眼睛中看不到深渊,只窥见围墙。冬眠野梨树初露端倪,枯草则更为彻底阐述制度体系、环境构造与人物行为间的互为因果消极的、虚无的,并最终指向社会道德水准与人类精神归宿。后段男女主漫长的争辩是摊开所有实验变量后的一次排演。还是怀念从前那些超验的神性时刻。